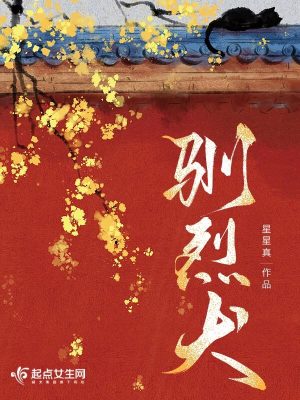沈宜亭从摘星院回来,先是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才带着白苏去明月轩看沈相静。
白苏对昨晚的事有些好奇,特别是主子彻夜未归,但沈宜亭只字不提,她也有眼见,嘴巴闭得很严,面对沈相静也未曾说起。
沈相静小腹已经隐隐有了鼓起的趋势,这些日子也没有出院子,就在院中待着,不时等着沈宜亭来同她聊聊天。
见沈宜亭今日来,面上有些憔悴神色,沈相静还有些担忧,生怕是前些日子妹妹那心事如今还未解决,正思索要如何开解她,就见沈宜亭似乎同紫苏白苏姐妹说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精神气与之前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沈相静一颗心暂且放心。
看来,是解决了。
她也带上几分笑容,等沈宜亭进来。
“阿姐,阿玺这些日子有没有闹腾过你?”
阿玺,是沈相静肚中孩子的小名。
孟琅曾为孩子取名,孟玺。
沈相静伸手贴了贴小腹,眼下甚至都感受不到什么,除了感觉身子稍圆润了一些,她似乎没什么变化。
倒是这些日子孕吐影响食欲,脸反而更尖了。
“阿玺可听话,今日硬是让我吃了一小碗饭,可算不容易。”
沈相静笑得眉眼弯弯,气质柔和。
紫苏是看着主子吃下去的,见状也笑了:“二小姐今日可来得晚了,不然若是陪小姐用早膳,定能看见,不止一碗米饭,还喝了小半碗汤。那汤是奴婢昨晚连夜熬炖,里头都快煮化了。”
明月轩自己有小厨房,就是为了能给沈相静做一些方便她吃的。
沈宜亭一想到自己晚起的原因,便有些心虚,忙将这个话题扯开,不愿多说。
“管家昨日来说,侯爷昨夜才回,雪中跪请三日,身子终究受了寒气,我便将你前些日子送过来的人参,命人熬了参汤送过去。”
沈相静说起这件事,面上也带了些忧色,“我听闻世子情况也不好,只是他那边素来同我们有些隔阂,也不好打听,紫苏问过管事,世子院中也没让人请府医去看看,不知是有事还是没事,真是教人心里担忧。”
沈宜亭劝慰她:“阿姐不必多想,侯爷眼下无碍便是万幸,若实在担忧,那我到时候抽空去替你瞧瞧。”
白苏听她这样说,神色突然变化,张口欲劝说小姐,却先被察觉到的沈宜亭瞥了一眼。
她马上便抿唇,低下头,不敢看沈相静,生怕大小姐看出不对问起。
“还有一件事我要同你商量商量”,沈相静换了个姿势,紫苏在她身后放了张软垫,好让她躺着舒服,“世子过几日便要率兵出征,候府没有什么女眷,你我虽暂住在此,旁人也中也便是候府能做主的女眷之一,眼下侯爷正病着,恐怕顾不上,我想着,若是我来替世子准备出征的行李,又觉得会让他多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沈相静比起沈宜亭大了许多,虽不如永威候那般年长,却也比江寺大出不少,勉强算是个大姐姐辈,对他有些怜惜疼爱,但也知道两人立场不同。
一来,她怕自己不懂军需,行李准备得不好。
二来,也怕江寺觉得她越俎代庖,手伸的太长,试图做侯夫人该做的事。
这件事沈宜亭也说不好。
江寺虽知道她们在候府是事出有因,但若是做了,未免有些指手画脚的意味。
她也拿不定主意:“不若这样吧阿姐,侯爷只是求了情便病得严重,要修养数日,世子定是也遭了大苦难,我便挑些好药材往摘星院送一送,顺便也看看世子情况,同他打听打听对这件事如何看。”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咱们事先打了招呼,他总不会再发难。”
沈相静思量一会,觉得也约莫只能这样。
“也可,过会我让紫苏给力送去一些药材,你一并送过去,免得请你帮了个忙,还要动用你的金库。”
沈相静打趣她。
沈宜亭爱药如命,自己多少留下了不少极其珍贵的药草,都被她收集起来,若是她送,那定然不是凡物。
沈相静是想同江寺示好,却不愿委屈了妹妹。
沈宜亭没拒绝,大不了她到时候再补贴进去,总归送东西的人是她。
从沈相静这边打了个招呼,好似便有了光明正大和江寺来往的理由,让沈宜亭心里放心不少。
反而是白苏有些闷闷不乐。
她本就不是愚钝性子,自从见了主子同世子关系匪浅后,再见她如此将世子放在心上,甚至大半夜不顾名声也要去摘星院看望,以致彻夜未归,便是傻子也明白。
可正因为如此,白苏心里才愤愤不平。
要她看,她家小姐便是天底下最才德兼备之人,圣人都比不上分毫,世子何德何能,焉能得到她另眼相待。
真是老天不公!
白苏这股怒气不能对小姐表现,也不好朝江寺发作,便都针对在翟墨身上。
因着沈宜亭带着大盒小盒的药送去摘星院,翟墨也礼貌的送了回礼过来。
加之江寺近日虽然养伤,但心腹都在肃清北策军内部事宜,虽不需他亲自出面,可也忙的很,有沈宜亭为他准备行李,反而省了不少事。
所以不时也往摘星院送谢礼。
大都打着吩咐的由头,让翟墨过去传个信,说是世子需要带什么,实际上全是为了和沈宜亭暗中来往的耳目。
为江寺收拾的行李全部交给管家清理,到时一并随军带走。
十月十七那天,沈宜亭带着一个小包裹,将一些伤药,混着危急关头能救命的东西一起,装好准备交给江寺,出门时,她看了眼桌面。
今日的佛经抄完还未整理,全部都堆在桌上,沈宜亭脚步一顿,转回去将佛经一一理好,看着一直放在自己这里的那块玉佩,只犹疑半晌。
江寺眼下一走,也不知何时回来,素来出征,短则数十天,长则十余年,她这些日子无论如何安慰,都逃不过动心的事实。
眼下就好像最后期限已到,一切欲回到最初一样。
不送出去,或许等他走了,内心那些悸动淡去,便也无所谓了。
若是送出去,显然便纠缠不清了。
沈宜亭站了许久。
临出门还是有些不忍心,转头将那玉佩扯下来,连同佛经一起打包塞进行李中,手上快速提笔挥毫,留下一张纸条给江寺。
若他往后受了伤,打开包裹取药时看到,便求这日夜开光的玉佩能保佑他。
此后莫要再受伤了。
也当是不枉费她抄了这么久的经书。
江寺眼下并不在摘星院。
北策军明日便要离京,这是圣上先前便下的旨意,并不因为他犯事而改变。
永威候过往对江寺都处于放养状态,他并非第一次出征,昔日同南抚军南征北战,行军已是家常便饭。
唯有此次不同。
“朝中纵使如何构陷,这些都伸不到军中,你出门在外,便不用理会朝堂上的斗争,只一心安定韩州,若是快些,我也好向陛下请命,让你早日回来,兴许一家人还能一并过年。”
永威候和江寺同在书房,二人对坐。
江寺眉眼有些像他,但因为融合了母亲的英气,所以更加柔和,永威候便是完全放旷的五官,面容威严。
他一贯不喜欢煽情,说出这样的话已经不易。
恐怕还是因为江寺遭了大罪,实在不放心。
江寺闻言,只点点头,目光在父亲已经斑白的鬓角看了看,心里有些沉默。
父亲与陛下年纪差不多,陛下已是风烛残年之貌,过往他总觉得父亲一夫当关,记忆也全是他风华正茂时,却不料原来已经逐见老态。
那日方正殿前,江寺从未想过他会站出来,一跪三日,大雪覆盖了鬓发。
“我明白。”
他沉下眸,似乎也不善于在长辈面前说这样的话。
“您大病未愈,明日便好生休息,不必出门相送。”
永威候却好像嫌这父慈子孝的温情颇为难受,听他说完便哼了一声。
“送你?可去你的,你又不是头一回出征,有什么好送的。”
他马上站起来,似乎嘲笑江寺自作多情。
江寺面色一下冷静,好像方才的动容丝毫不存在一般。
是他想多了。
永威候留他大致谈了谈韩州一事的见解,本想点拨点拨,但一番问下看,惊觉江寺洞察秋毫,行事果决,在南抚军那些年,并非是因为赵云铎这位世叔照顾,他心下欣慰,但父亲威严摆在这里,也不愿表露。
草草聊了几句,便将他放回去,让他今夜收拾好,明早天亮便启辰。
江寺从前厅回来时天色已经昏黄。
太阳测落,余下光辉正好打在院中,摘星院中金黄一片,像被人盖上一面金纱,朦朦胧胧,透着如梦似幻的静美。院外便被暗沉天色照着,凄黄叶片垂落,是浓秋的死寂。
二者对照一起,更显得院中那一抹亮色引人注意。
沈宜亭便在这片黄昏之中。
她正注视着日落,坐在院中石桌上,一只手托着下颌,不时看着飞过的秋鸟,便好像见到有意思的事物,面上淡笑几下。
江寺在院外,隐匿在暗色中显得更无声冷寂,唯有一双眼睛映着赤澄明华。
“沈宜亭。”
他远远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