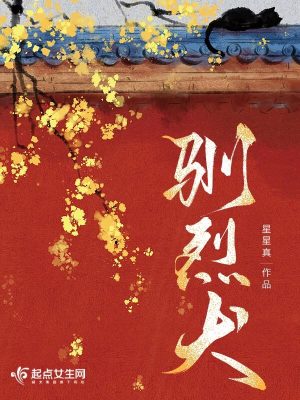沈宜亭终于注意到落在她身上炽热的目光。
她一转身就看见江寺缓步走来。
男人一身黑衣,行于夜色好像一柄待出鞘的极锋利的剑,寒刃挥开雾气缭绕,带着一身飒沓冷霜推开沉木。
“明日何时离开?”
沈宜亭站起身,他一进门,便问道。
江寺稍顿,正欲让她不必来送,便见沈宜亭垫了垫桌面。
“给你准备了药品,管家应该也备了,只是,我为医者,自然觉得我做的药,比旁人都要好,所以也为你拿了。”
她说话的姿态太得意,微扬下巴,带着一股骄矜。
江寺迟疑的话到了嘴边,都汇成一身笑意。
“好。”
“多谢沈神医。”
他远远拱手,朝沈宜亭轻推,躬身谢道。
这些时日未见他穿硬朗装束,反而打扮的如同翩翩公子,行世家礼节更显几分风骨,看的人眼热。
沈宜亭第一次送别他,心底情绪有些难明,只是她一向不显露,此刻也克制得好好的。
“不同你说这些闲话,我带了东西过来,将你身上的线取掉。”
“前往韩州路上,也多注意些,莫要让好不容易长好的口子又破开,到时可没人给你缝好。”
她说着,便朝着屋内走。
江寺缓步跟上,听出沈宜亭语气过分平淡,也意识到什么,只一个劲顺着她。
“好。”
“我一向听你的话,这些日子你说不动我便连府门也没出。”
他在床边坐下,抬手解开衣襟,边抬起头,黑沉的眼睛带着几分讨好神色,宛如一只凶狠的大型犬摇晃着尾巴向主人讨欢一般,看的人心软。
沈宜亭也软和下来,手下动作轻柔。
抽出的丝线和周围长好的新肉缠在一起,缓缓行径在其中,被抽动便带起一点点酥痒,像蚂蚁在身上爬动一样,并不疼,但就是让人难以忽视。
江寺眉头轻轻扯了一下,面上依旧沉着。
直到沈宜亭指尖轻点在伤口,他才惊讶般的抽了口气。
“嘶。”
沈宜亭忙烧灼似的抬手,担忧的看他:“弄疼你了?”
江寺扯着嘴角,笑容明朗:“没,就是没缓过来。”
沈宜亭见状,才又按下去,一点点试探内里伤口愈合情况。
细腻触感带着一股凉意,和男人充斥热意的躯体截然不同。
江寺好像一座大火炉,沈宜亭就是悬在上面的一块寒冰,时不时融化一滴春水,溅在炉中被灼烧,发出‘滋滋’火热的响声。
他眯着眼,有些餍足神态的感受着沈宜亭未曾表露的关怀和挂念,心里受用的同时,也不愿让她太过记挂。
“我明早晨出便走”,江寺看她收回手,也慢条斯理系上自己的衣裳,“你不必起来,天尚早,多休息。”
沈宜亭被他这样说,终于没忍住扁了扁嘴,她移开目光,转身收好东西,准备出门。
“我为何要起来,我又不会相送你。”
“自作多情。”
她说完,便甩手准备离开。
江寺见状,无奈叹了口气,脚步比脑子更快,忙大步朝前一迈,外袍衣带还未系好,上前长臂一伸,从沈宜亭腰间擦过,将人拦腰一挡,朝回一带。
他健壮的身躯宛如一堵墙,朝那里一立,沈宜亭便动不得分毫。
沈宜亭被他拦下,心里还有些愠怒,手握成拳,一拳打在江寺小臂。
“放开。”
她面容冷凝。
看江寺的眼神却带了几分怪责。
江寺看她不走,才将人松开,“我知道你是好意来送我,只是十里亭冷风吹的狠,便不要来受苦了。”
沈宜亭脸色更黑了。
难道她跟江寺的情谊,甚至不足以让她受一受盛京十里亭的冷风?
这人真是……太折辱人了!
太……
过分了……
“而且若你来了,我原本能利落干脆的走,恐怕也要步步回头,实在难舍下。”
“就当不要误了大军进程,沈姑娘如此好心,定然会答应的吧?”
江寺俯下身,在她面前展露一个清浅笑意。
沈宜亭心火乍散。
江寺说话倒是好听。
沈宜亭被她哄好,却不肯表现。
她见江寺衣带久久未系,抬手送到给他系好:“知道了。”
沈宜亭将一个竹子做的哨子悬在他衣带上。
然后便脚步极快的从屋内出去。
一路离开。
江寺出征那日,北策军点兵聚集,全在西山军营等候。
他一人披金甲,持长枪,黑盔覆面,座下一匹赤红汗血马,入宫请命后便独出盛京。
盛京十里亭,因一眼望断十里古道得名,是盛京看得最远的地方。
十月十八日,露华凝霜,十里亭覆白华。
沈宜亭沐月华,一路出候府,登九百九十九阶,上十里长亭。
一路共一千九百九十九步。
星霜京道见天晓,许我君郎不世功。
晨起,日头才冒尖,东方出现一抹明黄,像水墨画中映射金光,那金光朝周围扩散,越来越大,直到整个东天全然已亮,圆日垂悬,一抹紫气托日而现。
盛京城门短暂打开,沉重撞木声响起又落,一匹骁烈骏马疾驰而出,黑甲红缨被凛冽寒风吹动摇晃。
江寺厉目放眼前方,一路势不可挡,朝着西山军营疾驰。
沈宜亭一手握紧大氅,见他身影消失在古道之上,才从十里长亭最尽头,缓缓往回走。
走到台阶处,她望见长亭另一头一个伟岸的身影。
管家陪同永威候三更便候在这里。
“侯爷,世子已经走了。”
江寺声音最终汇成一个极小的黑点,在路的尽头彻底消失。
永威候目带几分沧桑神色,面容染欣慰笑意,他长叹一声,颇为高昂:“阿寺……不似我,似涅眉更多。”
“昔日涅眉惋惜女儿身无法成封狼居胥之功,而今阿寺可圆满遗憾。”
管家知晓永威候心中挂念的永远是当年同先夫人征战之时。
大雍刚立国,根基不稳,先帝纵有一腔谋略,受限于各地起义,叛乱。
他便同先夫人,如今陛下一同,出征镇压,为大雍开疆扩土。
而如今,这位战场上的虎,必须沉浸在权政之中。
除他之外,无人再能让帝王有着片刻清醒。
沈宜亭远远看了一眼,因着不愿与永威候撞见,届时不好解释,便先走一步。
永威候落后她许多,迟迟没有再动。
二人皆不知,已经走过十里古道的红缨晃动着,在路的尽头停下。
江寺勒马回头,一眼收揽十里亭所有风光。
除了远行之人,无人知十里古道尽头,也能看到十里亭全部景貌。
昔日十里亭上空荡寂寥,而今有人将他牵肠挂肚。
江寺从西山军营领兵出发,青毫作为副将,引马跟在他之后,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北策军。
北策军经历一次大换血,而今将领士兵,皆是江寺心腹,各个都是数一数二的精锐,同他关系极好。
但除了青毫,无人敢开将军的玩笑。
青毫从出发开始,耳边便有一声鸟鸣,他听得实在刺耳,本在秋后出征,能不能过年都是二话,偏那鸟一声声叫得心烦意乱。
一边江寺倒是兴致大好,虽一贯面无表情,但周身都有一股洋溢欢心的氛围。
看得青毫多有羡慕。
“将军”,他觉得,这糟心的鸟鸣,混着糟心的鸟,一并都要处理了,“随军粮草可够?不如我们在路上猎点野食过去,韩州那地方,地处极北,恐怕到时候吃不到肉喽。”
吃肉,一向和喝酒一样,是能让军心沸腾的好东西。
这两个字一出,身后的部队便躁动起来。
北策军脚步依然整齐,面容仍旧坚毅,就是紧抿着的嘴一个两个都张开乐呵。
有人实在忍不住,问青毫:“副将,哪有肉啊,不若我请命,离队一息,去弄回来给兄弟们打牙祭!”
江寺闻言,瞥了眼他,说话那人立马老实,脸色严肃的宛如雕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青毫咳了咳,好笑的指着上头:“将军,不是我嬉皮笑脸,都怪这鸟,叫得我实在是烦。”
“不如将军允我拉弓,保管一眨眼就射下来,绝不耽误行进。”
青毫被江寺眼刀扫过,顿时也怂,但又不甘心放过那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江寺抬头看了一眼。
半空盘旋的那鸟实在是快,从离开十里亭开始,江寺便注意到它一路跟着,原以为是迁徙的鸟类,却不想它竟然全程跟随北策军,一步未曾落下。
江寺心中奇怪,被青毫一指,才好好看了看。
那鹰隼察觉到底下的目光如箭一般,身姿也往下飞了飞,飞底好叫人瞧见他的矫健。
江寺看得更清楚。
那鸟实在眼熟……
真是……太眼熟了。
若是鸟身上羽毛换成红色,头顶那一黑点变成白点,便真是一个翻版的红角鸮。
他脑子好像被人一鼓槌敲醒,突然想起沈宜亭昨日挂在腰间的那根竹哨。
江寺心底略激动,面上露出一个笑。
点点白牙咧开,转头看向青毫,那牙跟要撕碎他似的:“射你个头,你敢吃它,将军我便拉弓,一息把你射下来。”
青毫一愣,刚想辩驳几句。
说清楚他打下来纯粹是为了给将军加餐。
就见江寺一抬手,“停。”
身后大军一秒立正,皆驻足停于他身后。
江寺从脖子上将那根竹哨拉出来。
沈宜亭送的东西都被他妥善保管,就算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哨子,他便觉得也是个念想,准备带在身上,所以给穿了根线。
青毫不明所以看着他。
只见江寺一只手将竹哨置于唇边,另一只手学着头一次见,沈宜亭招赤哥的模样,朝前略举了举。
“咻——”
竹哨被吹响,发出尖锐的声音。
天空中,鹰隼似乎感觉到召唤,仰头长啸一声。
浑厚鹰鸣穿透长空,将底下所有人的注意力皆攫取过去。
它盘旋在天空,庞大身姿和尖锐利爪皆被惊艳注视。
“好俊的鹰!”
“真是骁健啊,你看那喙,恐能洞穿盔甲。”
底下士兵议论,便见红角鸮转悠几圈,朝下俯冲,安稳落于将军手上。
青毫惊呆:“将军!!”
“这是您养的鸟?!”
好家伙,他只见红角鸮又大又肥,眼下才发现它毛发光滑,喙羽锋利,姿态英勇昂扬,一看就是一把打仗的好手。
到时候专门啄眼睛,爪子抓脸,糟心死那群胡贼!
江寺有些骄傲的扬了扬头,又矜持的应了一声:“嗯。”
他看见红角鸮脚上绑着信条,便取了下来。
红角鸮从他手上飞下去,便盘旋绕着他飞动,一路随着军队前往韩州。
“继续。”江寺下了令,在最前方看起了沈宜亭写来的纸条。
【江寺:
红角鸮,名兰庭,与赤哥一巢生。生而好战,可连飞三日不歇,耐力极长,传讯皆用此。
沈宜亭留。】
他抬手抚了抚兰庭,眼中夹杂着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