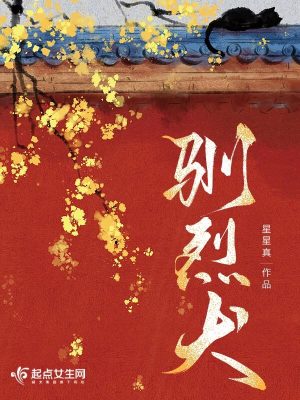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世子”,沈宜亭走近,见他偏头不动,也跟着歪了歪头,叫了一声。
江寺被唤回神,眨了眨眼,点头应下,而后指着身侧:“坐。”
沈宜亭瞥了眼他指的那处,草木还在朝上生长,叶片上隐约带着一些水汽。
沈宜亭愣了一秒,笑了笑,便准备坐下。
江寺一直注意着,见她怔愣,也意识到沈宜亭不是西山军营那些士兵,也不是同他混迹在一起不拘小节的好友。
她虽在盛京江南都不如何有名,但通身气度着实称不上普通,想来也是大家闺秀的教导出身。
让人露天席地而做,实在是有些失礼。
江寺反应过来,刚想问她需不需要支张椅子,就见到沈宜亭将手中灯笼火光灭掉,放在一边,就这他手指方向,稳稳落座。
她坐下之后,瞥了眼江寺欲言又止的模样,心里对他所想有了估计,便主动笑了笑,道:“世子不必多想,我并非重于礼法的人。”
她说完,便看向面前火堆中已经烤的十分香的羊羔。
羊肉表面泛出一点焦黄,外层不知道被江寺涂抹了什么调料,在肉质之外似乎形成一层珠光一样的膜,一股股甜香夹杂着羊肉特有的味道,勾的人口腹之欲大涨。
沈宜亭挑了挑眉。
她还以为江寺说的请她吃只是客套话,没想到这人真请了,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沈宜亭还没吃过这样的方法做出的肉。
她有些好奇看了几眼,看了看正在炙烤的肉,又看了看江寺,真心实意夸道:“世子真是,奇思妙想。”
江寺嘴角勾了勾,短暂笑了一下,很快便放下。
“这种吃法在军中很流行,盛京之中应当没见过。”
他解释道。
沈宜亭常听人说永威侯世子常驻西山大营,实际上在考入西山大营北策军之前,江寺一直随同三军四处征战。
他是实打实靠着军功和实绩成为北策军的少将军,而不是因为父亲的荫庇。
沈宜亭听他提及,盯着跳动火焰的目光隐隐流露出一丝羡慕:“真好,世子常在军中,定然也随军见过许多的风土人情。”
江寺听出她语气中的羡艳,一时多看了眼她,见沈宜亭双膝合并屈起,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下巴便搁在那只手上,注视着火焰,神色认真不似伪装。
男人心里突然有了很奇怪的想法。
沈宜亭似乎觉得他好似很了不起。
“随军见过不止风土人情,也有世事百态,我曾随南抚军南下靖边,一条路横跨渡江,从盛京一直跨越江南,并州,幽云等地,一路见识盛京无边繁华富庶,然而到了靖边之外,人人身着屡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是吗?”沈宜亭轻轻呢喃,江寺原以为让她认识到随军残酷,能打消她心中小姑娘般的美好幻想,以免将出征当成游玩般轻视,却没想到沈宜亭突然笑了笑,完全将话题方向转了个向。
“我倒是很羡慕,只可惜我生来便是女儿身,向来被禁足在家,熟背女戒女德,无法征战沙场,亦难以于朝堂搅动风云。”
搅动风云四个字被她轻轻吐出来,带着一股无言的气势。
江寺有一瞬间在沈宜亭眼中看到了野心和展望,那是一种他极其熟悉的不得志的感觉。
这种不得志并非来自于自己能力的欠缺,而是来自于现实。
就像他一样,无论做出多少努力,似乎在外人眼里都只是因为有一颗参天大树的托举,才有他如今的盛名,甚至于连参天大树本身都如此认为,始终当他只是树荫下的小苗,将他护佑其中,不告知半点风雨。
沈宜亭看着火光,确实被勾起了几分不愉快的回忆。
沈宜亭年少时,是在自家请的先生教学,只因在学院中,她不似其他小姐一般爱听风月韵事,也对女子戒律不放在眼中,反而偏爱兵书奇略,政事沉浮。
这事传到她爹眼中,就成了女子乱国的前兆,这位全天下儒生敬仰的大学士,在女子入仕一事上有着格外坚持的态度,他夸奖也震惊于沈宜亭对朝政的敏锐,也奇异于她轻而易举能够看透人心和阴谋的能力,但也无比坚持于,她身为女儿的可惜。
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让这位女儿不在外发表她那过于惊人的朝政见解,沈宜亭此后便被禁足在府中,由专门的先生教学,主要课程便是女子本分。
他爹为了打消她妄图参与朝政,实在是做出了不少努力。
然而最后也没能彻底将她与风云诡谲的朝堂彻底斩断孽缘。
“我母亲亦是女子”,江寺定定看沈宜亭泄露她眼底浓郁的渴望,突然出声打破沉凝的气氛,他语气轻松,提及先夫人时带着几分怀念,“她也曾是三军中,令人无比敬佩的巾帼女将。”
沈宜亭抬头,江寺目光闪烁着,嘴角带着温柔的笑意,提及母亲,他似乎也短暂放下心防,将沈宜亭当成了一个普通的,能够一同吃肉喝酒的好友,和她阔天海地谈着自己的所思所想。
“我倒不觉得女子生来便比男子差,正要论,我爹的功夫甚至不如我娘,兵法谋略也稍逊,幸好我从小由我娘手把手教导,否则能不能有如今的出息尚且不定。”
江寺毫不留情的贬低永威侯。
但他说的也大多是实话。
永威侯其人实则并不出色,行兵打仗他不如赵云铎,论用人知事不如慎王,甚至论起朝堂尔虞我诈,也比不得内阁大臣顾杞年。
但他心思纯正,尤其忠诚,脑子一根筋,认定了就要走到底。
这是为数不多的,也是帝王最看重的优点,所以他才能日复一日,如日中天,成为帝王最亲近、信任的重臣。
“只不过,沈姑娘若真的参军”,江寺看了眼她,话音一转,突然有些调笑,“也只是充当军师一样的职位,你实在太聪慧,怕是主将不敢将你放在战场那刀剑无眼的地方。”
江寺说着,偏头看了眼她。
沈宜亭从他的话中听出来另一层意味。
先夫人武艺高强,为人有胆有谋,所以为一军将领,立下赫赫战功。
她手无寸铁,更适合于人之后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就比如现在。
江寺看似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一切都能从他所见的蛛丝马迹中,推测出全貌。
沈宜亭看他动作干脆的片下一块肉,另一只手不止从哪里掏出来一块干净的阔叶片,炙肉被安妥的放在叶片中,然后朝她递过来。
男人动作仔细,也格外细心。
“世子又未尝不是,见微知著,恐怕要更甚于永威侯。”
沈宜亭接过,轻声细语道。
江寺手上动作不停,刀刃片下肉后,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短刃利落插进去,然后就着刀尖送入口中。
“见微知著?”他语气淡淡,抬眸看向沈宜亭,那双冷锐的眸光显得格外森冷,“沈姑娘所谓见微知著,不过是江寺不愿被蒙在鼓里,旁人半点不曾告知,所以只好自己费尽心思推敲。”
话已至此,江寺也没有继续遮遮掩掩,直白的同她道:“就像你和我父亲筹谋一样,若不是从你身上看出我父亲态度不明,我也不会知道所谓的侯夫人只是掩人耳目的理由。”
“他从不肯告诉我半点,若我自己不细心,坠马一事中,也就成了其他人的棋子。”
江寺抿了抿唇。
他厌恶受人摆布。
沈宜亭被他一番话震在原地,原来永威侯连亲生儿子都不告诉,难怪她刚开始向江寺说起时,对方意味不明问她永威侯是否知道。
沈宜亭敛眸,这事她不能多嘴半句,说起她反而也是其中帮凶。
只是望见江寺神色寥落,心底还是不自觉生出几分动容。
江寺没在意,仍旧将她照顾得极好,二人分食一只羊羔,沈宜亭食量小,吃了几口便吃不动了,只好同江寺告辞,临别时留下一些药作为回礼。
对面的人一走,江寺视野便开阔起来,他看了眼被女人坐下时压弯的叶子,神思不明。
沈宜亭敏|感的察觉到,自从那日夜聚之后,她和江寺似乎有了一种无形的牵绊。
具体表现在,原本需要花费一番功夫打探到的消息,江寺若是知道,总能在第二天送来。
经常她一觉起来,窗棂上便多了个熟悉的木匣子,匣子里放着几份文书,记录着她所需要的消息。
江寺分明还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好像就因为她那天透露的一点念想,于是便着手找了这些材料。
沈宜亭再一日看到窗棂上的木匣,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这人是觉得她同先夫人相似,所以才多有相助么?
江寺其实没想这么多。
他知道沈宜亭和父亲有一些计划,具体虽然不知道,但还是有心想帮忙,其实多少心底也存着几分向永威侯证明自己的心思。
虽说父亲严防死守不让他知道,那他偏要插手,他倒要看看父亲要多久才能意识到,计划中已经有了他的痕迹。
这些都是江寺的小心思,帮助沈宜亭也在其中罢了。
但沈宜亭没想到她能在一天之中收到两份重要的文书。
一份自然是早晨江寺偷送来的。
另一份却出人意料,竟是凌霞郡主邀她入府赏花。
实在是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