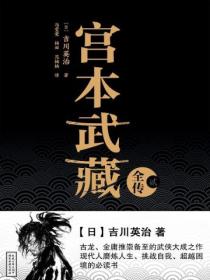02
他同时挥起垂着的刀,向这些土匪迎面杀去。
“哇”的一声轰响后,就再分不清谁是谁了。一群人像被卷在小旋风中的羽蚁一般,混战就这样开始了。
这条路,一边是水田,一边是种着树木的堤。这样的地形对土匪来讲是不利的,但是便于武藏进退自由。这些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土匪,拿的武器也是杂乱无章的——跟一乘寺本殿西侧古松旁的决战比——这场战争完全不足以让武藏有生死之战的感觉。
可能也是因为他在时刻想着怎样找机会撤退。与吉冈门下那群人打斗的时候,没有过一点“后退”的想法。现在是不打算与他们不分胜负地打下去的,只想用兵法上的“策略”引他们上钩。
“啊,这家伙——”
“想逃跑——”
“不要跑——”
土匪们锲而不舍地向逃跑的武藏追赶而去——不一会儿就被武藏带到了原野的一端。
这儿不比刚刚那条相对狭窄的路,宽阔的原野看起来会使武藏陷入劣势。武藏向那边逃、这边跑,诱使原本聚集成堆的土匪分散了不少。
突然,武藏变成了攻势。
“咔……”
一下!
又一下!
武藏的身影在不断飞溅的鲜血中穿梭。
也许将此时的情形形容成像砍竹竿一样也并不夸张。被砍伤的人,大部分都很狼狈地丧失了神智。砍人的人,像进入了无我之境一样,反复地进行着砍杀的动作。土匪们顾不得形象,蜂拥朝原路逃回。
五
“来了——”
“来了哦——”
在道路两旁阴暗处隐藏的村民,确认土匪逃来的足音已到附近后,“哇”的一声蜂拥而起。
“妈的!”
“畜生!”
村民们挥舞着竹矛、棒子等武器,冲杀上去。
随后,当有“快隐藏——”的命令时,村民们又伏下身子,等待后面两两三三的土匪过来后,再发动下一次的进攻。
“浑蛋!”
像治退蝗虫一样,大家集众人之力,将土匪一个一个地打倒。
村民们看着这些成为战利品的土匪尸体,瞬时变得更加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意识到原来自己拥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
“又来了!”
“一个人!”
“来吧!”
这些村民马上聚成一团,做好迎战准备。
这次跑来的是武藏。
“哦,不对不对。是法典之原的那个流浪武士。”
他们就像迎接主将的士兵一样,退到道路两边,凝视着武藏那泛着朱红色的身影和手里的那把血刀。
血刀的刀刃已经破损成锯齿状。武藏将这把刀扔掉,捡起了落在身旁的一把土匪的矛。
“你们也将这些尸体手中的刀或矛,用作自己的武器吧!”
年轻人听到武藏这样说,争先恐后地拾起武器。
“好了,之后就看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将土匪赶走,夺回自己的家园和家人。”
武藏一边鼓励着他们,一边身先士卒冲向村子的方向。
已经没有一个村民显露出胆怯了。
就连女人、老人和孩子都在年轻人之后拾起了武器,跟上武藏。
进入村子后,发现比较大的农家都已经被烧了。村民、武藏、树木、道路都被映成了红色。
燃烧着房子的火似乎已经蔓延到竹林了,青竹的爆裂声,“啪啪”
地夹杂在火焰中,凄厉而清脆。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因大火而发狂的牛也在牛棚中惨叫着——可是,在不断散落的烟灰中,并没有发现土匪的影子。
武藏突然想到了什么——
“是哪里飘散着酒香?”
村民们都沉浸在这漫天烟雾的哀痛中,没有感觉到什么酒的味道。
经武藏这样一说,才反应过来。
“只有村长家用酒瓮储存了很多的酒。”
武藏推测土匪一定是聚集在了那里,于是跟大伙儿讲了自己的策略。
“跟我来——”
这次的目标是村长家。
此时从四面八方返回村子里的人已经有上百人。躲进地板下、草丛中的人也都陆续出来了。团结演化成强大的力量。
“那是村长家。”
这些村民远远地指着那所被所谓土墙围起来的住宅。这所住宅在这个村里算是大型的了。
走近这个村长家,就像喷出了酒之泉一样,酒香扑鼻。
六
村民们在附近躲了起来,武藏则越过土墙,翻进了这个被土匪作为根据地的农家。
土匪的首领和主要人员在这间土屋里,醉醺醺地搂着女人饮酒作乐。
“不要慌——”
土匪首领似乎正在发着脾气。
“只是出来一个多余的人,没必要我们出手,你们把他给收拾了。”
说着这样的话,将那个来报信的手下骂得狗血喷头。
这时,那个首领突然感觉到外面有什么异样的声音。撕着烤好的鸡肉,仰头饮酒的其他土匪也都僵住了。
“呀,怎么回事?”
他们的手下意识地摸向武器。
一瞬间,他们的心里一片空洞,只顾注视着传来惨叫的门口。
武藏这时马上跑向房间的侧面,找到正房的窗口后,以矛柄为支点,翻身从窗口跃入屋内,正好落在首领的身后。
“是你吗,土匪首领?”
首领循声向后望去的时候,武藏的矛已经刺穿了他的胸口。
这个狰狞的男人,“哇”的一声大叫,血汩汩地从胸口涌出。武藏轻轻一松手,这个人便带着矛一起跌倒在地。
此时武藏的另一只手中已经握了一把从刚刚冲上来的土匪手中夺来的刀。紧接着,一个土匪被砍伤、一个土匪被刺死。土匪们见状就像马蜂出巢般,忙不迭地向土屋外面跑。
武藏将刀掷向这群人,紧接着又将那把矛从死尸的胸口拔出。
“别跑——”
武藏就像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般——横握着矛向外冲去。然后如同竹竿打水般,搅开了土匪群。外面的宽阔为矛的自由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武藏用力抡着矛,橡木矛柄都微微弯曲了。忽而将匪群冲散,忽而从上向下劈下来。
抵挡不过的土匪们向土墙门口逃去。因为外面守着武装好了的村民,刚跨出门口的土匪,就又遭受到了另一番攻击。
结果,很大一部分土匪被村民杀死。即使有逃走的土匪,也几乎都肢体不全了。村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生来第一次高唱起了凯歌,旋即和孩子、妻子、父母抱成了一团,喜极而泣。
这时,不知是谁在后面说了句:“怕是随后会有场可怕的报复。”
村民们因这句话,立刻沉寂。
“他们已经不会再来这个村子了。”
武藏说道。听武藏这么一说,他们终于又恢复了安心的样子。
“但是,你们也不要从此变得狂妄自大。你们的职责不在拿起武器,而是铁锹。如果误以为从此可以滥用武力的话,会有比土匪更可怕的天谴降临的。”
七
“看清情形了吗?”
住在德愿寺的长冈佐渡一直没能入睡。
从原野、泥沼的另一端也能很容易地看到村里的大火。现在火焰看似已经被扑灭了。
两个家臣说:“嗯,看清了。”
“土匪已经逃跑了吗,村里的受害情况怎么样?”
“我们赶到时,村里的人已经亲手杀死了大半的土匪,其他的土匪都跑散了。”
“真的吗?”
佐渡一副讶异的神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主人细川家的领土民治一事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已经晚了。
佐渡走到床榻前。想到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回江户了,说道:“我想去那个村子转转。”
说着,又向马厩走去。
德愿寺的一名僧人跟上来负责带路。
到了村子里,佐渡回头望着两名侍者,不可思议地问:“你们昨晚到底看清楚没有。这些路上躺着的土匪真的是百姓杀死的吗?”
村里的人没有睡觉,他们在收拾烧毁的房屋和尸体。一看到骑马而来的佐渡,都赶紧纷纷地躲进屋里。
“啊,这应该是有什么误会。谁找一个能讲明白话的村民出来?”
于是德愿寺的僧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带过来一个人。佐渡这才弄明白昨夜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是这样啊!”
佐渡点着头。
“那么那个流浪武士,叫什么名字?”
不管佐渡怎么问,跟前村民都答不上来,说是没有问过他的名字。
不得已,僧人只好去别处询问。
“听说是叫宫本武藏!”
“什么,武藏?”
佐渡想起了昨晚那个孩子。
“那么,就是那个孩子口中的师傅了?”
“平时,这个武士会领着那个孩子开垦法典之原的荒地,做一些百姓做的事情,真是个奇怪的武士!”
“想见见那个男人。”
佐渡嘟囔道。突然想起藩邸还有要紧事。
“下次再来。”
说着策马而去。
到了村长家的门口,佐渡被一块告示牌吸引驻足。这块崭新的告示牌上的墨迹还没有干透,上面写着:村里人应该时刻铭记的事
铁锹也是剑
剑也是铁锹
耕种土地的时候,不要忘记战斗
战斗的时候,不要忘记土地
二者要合二为一
不要违背常理,走错路
“哦……是谁写的这块牌子?”
村长应声出来,伏地而答:“是武藏大人。”
“你们能明白吗,这些字中的道理?”
“今天早晨,将村里的人召集在一起,请武藏大人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已经差不多明白了。”
“小师父。”
佐渡扭过头。
“可以回去了。辛苦了。非常遗憾,这次来去匆匆。还会再来的,告辞!”
说罢,佐渡继续向前奔驰而去。
卯月之时
一
主君细川三斋公一直在丰前小仓的本地,没有在江户的藩邸待过。
在江户有长子忠利和辅佐的老臣,细川三斋公也无须操心许多。
忠利才智过人。年纪虽还不到二十,却即使身处在以新将军秀忠为首的移居新城的枭雄和豪杰大名中,也不会给父亲细川三斋公丢脸。他的年少气盛、对时代的洞察力,远远胜出那些从战国时代走来的、整天夸耀自己本事的徒有胆量的老大名。
这会儿书房和马场上都不见忠利的影子。
藩邸的占地很广阔,庭院等还没有完全修整。有一部分还保持着原来的树林的样子,一部分被建成了跑马场。
“少主正在那里玩吗?”
佐渡在从马场返回的路上,向一名路过的年轻侍卫问道。
“在练箭场。”
“哦,在摆弄弓箭啊!”
穿过林荫小径,朝练箭场走去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听见,“嗖”
的一声,箭飞射而出的声音。
“喂,佐渡大人——”
一个人叫道。
叫住佐渡的是同藩的岩间角兵卫。他是一个很有手腕的实干家。
“您去哪里?”
角兵卫走过来。
“去找少主。”
“少主现在正在练习弓箭。”
“有些要紧的事,即使在练箭场,也需要汇报一下。”
角兵卫正要通过佐渡身旁时,突然又说:“佐渡大人要是没什么紧急的事,有点事想商量一下。”
“什么事?”
“我们就找个地方说一下。”
说罢,环看了一下四周。
“去那边吧!”
角兵卫将佐渡请进了树林中的一个侍从休息茶室内。
“不是别的,就是在您和少主谈起什么的时候,想请您借机推举一个人。”
“是想在这一家当差的人吗?”
“我知道有很多到佐渡大人您的府上请您推举的人。但是这次这个人和您府上的那些人是不太一样的。”
“哦……少主也在谋求人才。但是都是些只想混个工作的人啊!”
“论资质,这个人和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事实上,他和我家里还多少有些亲戚关系。从岩国来我家里已经两年了,应该是藩内所需要的人才。”
“如果是岩国的话,曾是吉川家的武士吗?”
“不是,是岩国乡间的一个孩子,名叫佐佐木小次郎,虽然还年轻,但是曾跟随钟卷自斋学习过富田流刀法。在神速拔剑法方面,还得到过吉川家的食客片山伯耆守久安的真传。而且,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自创了岩流流派。”
角兵卫竭力向佐渡推荐这个人。
不管是谁推荐任何人,都会这样费尽唇舌。佐渡并没有多热心去听。他反而想起了另外一位因为自己公务繁忙而拖了一年有余、最终忘记推举了的人。
这位就是开垦法典之原的宫本武藏。
二
武藏这个名字,从那件事以后,就一直深刻在他的心里。
(如果武藏那样的人能供职于这里就好了。)佐渡在心里暗自琢磨。
他曾想再去法典之原一趟,进一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人,然后推举给细川家的。
现在——回想起来,自那次从德愿寺返回的那一夜起,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一年有余了。
因公务繁忙,一直没能有机会再去德愿寺参拜。
“怎么样?”
在佐渡想起武藏时,岩间角兵卫再次将自己府上的佐佐木小次郎的履历和为人强调了一下,满怀期待地希望佐渡能助他一臂之力。
“您见到少主后,拜托,给推荐一下吧!”
“好的,知道了。”
佐渡回答道。
反复拜托后,岩间角兵卫转身离去。
但是此时比起角兵卫提起的小次郎,佐渡的心里还是更放不下武藏。
到了练箭场后,少主忠利正在和家臣饶有兴致地拉弓射箭。忠利射出的箭,每一根都能很精准地射到靶心,连出箭的声音都彰显着气势。
他的侍从有时会劝谏说:“当今战场上,最常用的武器是枪、矛,大刀、弓箭等是要被淘汰的。若要将弓箭作为武士的装饰,也只需要知道射法就行了。”
忠利每当此时就会反问:“我射箭,是以心为靶的。你看我像是为了在战场上,射击十或二十个武士而练习的吗?”
细川家的臣子们闻之心服口服,他们虽然对三斋公大人的佩服是没话说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三斋公的缘故而侍奉忠利的。忠利身边的近侍都是真心将忠利当作明君来看待的,无关于三斋公是否了不起。
这虽然是后话了,但是这件事能证明藩臣们到底有多敬畏忠利。
后来细川家被从丰前小仓移封至熊本时发生了一件事——在入城仪式上,新城主忠利穿着简便朝服,在熊本城的正大门处走出轿舆,于粗席之上向熊本城参拜——这时,忠利的冠冕绳带碰到了城门的门栏上。
从此以后,忠利家的家臣、侍从通过这个门的时候,便不会从正中间跨过去。
这足可见,当时一国的国守对于“城”抱有多么严肃的态度,家臣对“主”是多么的尊崇。从壮年时代开始,忠利就有如此气概。向这样的君主推荐家臣,是不能粗心大意的。
长冈佐渡来到练箭场,看到忠利后,开始为自己刚刚和岩间角兵卫分别时,草率答应的那句“好的,知道了”而感到后悔。
三
站在年轻侍从当中,因比赛射箭而汗流浃背的细川忠利,依旧是一副不拘小节、与周围侍从无二的样子。
这会儿,忠利正和侍臣们说笑着走进练箭场的休息室,擦拭着汗水。一抬头发现了老臣佐渡,便玩闹地邀请道:“老爷爷,要不要也试着射一下。”
“不了,你们太孩子气。”
佐渡也开玩笑道。
“什么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把我们看作孩童?”
“我的射箭水平,不论是在山崎合战,还是在控制韭山城的时候,都受到了您父亲大人的赞许,得到了公认。现在是不会在一群孩子中寻求安慰的。”
“哈哈哈哈,又开始了,佐渡大人的自吹自擂。”
侍臣们笑了起来。
忠利也一阵苦笑。
顿了顿。
“有什么事情吗?”
忠利恢复了认真的表情。
佐渡稍讲了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然后问道:“岩间角兵卫好像是想推荐什么人,您听说了吗?”
忠利摇了摇头说没有,随即马上想起了什么。
“对,对。是一个叫佐佐木小次郎的人,他提过几次,但是我一直还没见到这个人。”
“那要不要召见一下呢,诸家都在高薪求贤?”
“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是啊,要不先召见一下看看?”
“佐渡。”
“是。”
“角兵卫又拜托你来说了吗?”
忠利苦笑。
佐渡也深知这位年轻主人的英明敏锐。自己再怎么多嘴,也不会影响他的判断的。所以只是笑着说:“您的意思是……”
忠利将弓拿在手上,一边从侍臣手中接过弓箭,一边说道:“角兵卫推举的人我想看看,同时,我也想找时间见见你所提到的,那场夜间事件的主角武藏。”
“少主您还记着呢?”
“我是记着呢,你是不是都给忘了?”
“没有,因为在那之后我一直没能找到再去德愿寺参拜的时机。”
“为了得到一名人才,即使再忙也应该抽出时间去看看。等做完其他事情再说这样的想法,可不像爷爷你的想法呀!”
“实在抱歉,但是,各方来投奔的人非常多,前来举荐的人也很多,少主您已经应接不暇了。我也就在给您讲过这件事情之后,不知不觉地有了些怠慢。”
“别人的眼光我不清楚,但是爷爷你的眼光我是相信的。你举荐的人,我非常期待。”
佐渡诚惶诚恐地从藩邸回到自己的府内后,立即备马,只带上一名侍从,就向法典之原出发了。
四
今天晚上不能停留,应该马上直奔目的地。因为心里十分着急办这件事,长冈佐渡绕过了德愿寺。
“源三。”
听到叫他的名字,这名侍从回头望去。
“这附近就是法典之原了吧?”
侍从佐藤源三答道:“我觉得应该是了吧——不过这里还能看到青翠的农田,正在开垦的地方,应该还在原野稍微靠里的地方吧?”
这里已经离德愿寺很远了——如果再往里走的话,就接近常陆路了。
快接近黄昏了——农田上面的白鹭像粉末一样飘散着、飞舞着。在河滩的边缘、丘陵的背面,到处种着大麻、麦子。
“啊,老爷!”
“怎么了?”
“那里聚集着很多农夫。”
“……噢……果然。”
“我去问一下怎么回事吧?”
“等下——看他们在轮流叩头,应该是在拜着什么呢吧?”
源三下来牵着马的缰绳,一边试探着浅滩的深浅,一边引导着主人的马向前走。
“喂,百姓们。”
听到叫声后,他们吃惊地向这边望了一眼,原本聚作一堆的状态也被破坏了。
前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屋。小屋的旁边是像鸟的巢一样的一个佛堂,他们刚刚就在参拜这个佛堂。
大概五十名左右结束了一天辛苦劳作的农民,拿着清洗过的工具,打算参拜完后便回家。这会儿见到有旁人过来了,吵吵嚷嚷议论起来。
有一名僧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您好,您好,我还在想是哪位大人来了呢。这不是长冈佐渡施主吗?”
“哦,你是去年春天,村里遭遇骚乱时,为我做向导的德愿寺的僧人吧?”
“是的,今天您也是来参拜的吗?”
“不是不是,只是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赶紧赶了过来。要是参拜的话,之前不是都会直奔寺里的吗?想打听一下,当时在这里进行开垦的那个流浪武士武藏和小孩儿伊织,现在还在吗?”
“武藏大人,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
“什么,不在了?”
“是的,大概半个月前,不知道去哪里了。”
“怎么回事,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开的吗?”
“不是……只是,那一天,因为之前一直发大水的荒地终于变成了青青良田,乡亲们高兴,都来祭祀——之后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武藏和伊织就离开这间小屋了。”
这名僧人至今还是不敢相信武藏已经离开了——他跟佐渡讲起了详细情况。
五
自那以后。
惩戒了土匪,稳固了村里的治安,每个人的生活回归了平和,村里没有一个人再直呼武藏的姓名。
——法典之原的流浪武士。
——武藏大人。
之前一直将武藏当作疯子经常说他坏话的人,也来到他的开垦小屋里。
(让我也来帮您吧!)
这些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藏对谁都一视同仁。
(想来这里帮忙的人就来帮一下。想过富裕生活的人也尽管过来。
只自己吃独食的人等同于鸟兽。至少,也要为子孙们留下一些劳动成果。)
这样一说,大家马上都积极响应。
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名能空出时间的人聚集在他开垦的田上。农闲时期,甚至能来上百人。大家齐心协力,开拓荒地。
最终,去年的秋天,制止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水患。然后,冬天开垦了土地,春天播撒种子、引水灌溉。到初夏的时候,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新田地也算是绿油油一片了,稻子随风沙沙作响,麦子长了一尺来高。
土匪也不来了。村里的人辛勤耕耘。年轻人的父母、妻子将武藏当作神来崇拜,会及时将糕点或新鲜蔬菜送到武藏的小屋里来。
来年,旱田、水田的产量都会成倍增长的。再下一年会长三倍的。
村民们在对讨伐土匪和维持村里治安抱有信心的同时,对于荒地的开垦也开始抱有极大的信心。
出于感谢之情,村民们休假一天,带上酒壶来到小屋,团团围住武藏和伊织,配合乡村神乐的鼓点和笛声,举行了一场青田祭祀。
这时,武藏说:“不是我的力量,是大家的力量使这里有了现在的收获。我只是调动了大家的力量而已。”
然后,他又对碰巧遇到这场祭祀的德愿寺僧人,说道:“像我这样的一介漂泊武士,大家如此信任依赖我,使我很不安——为永保信念,还是把它作为心灵的依托比较好。”
说着,武藏从包裹里掏出一座木雕的观音像,交给了僧人。
第二天一早——武藏就已经不在小屋里了。他带着伊织不辞而别。
应该是在黎明前走的,连旅行包裹都没有打。
“武藏大人不在了!”
“不知去哪里了!”
村民们像与慈父失散了般,当天,不再有心情干活儿,他们谈论着武藏,陷入一片惋惜之中。
德愿寺的那名僧人,想起了武藏的话:“我们不能这样停滞不前。
不要让田地荒废,要想办法继续增加产量。”
僧人对大家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在小屋的旁边搭建一间小佛堂,并将观音像放进去供奉。村民们自发地每天早晚在工作开始前和工作结束后去那里参拜,就像去跟武藏打招呼一样。
僧人的话说完了。
长冈佐渡怀着无限的悔意:“……啊,已经迟了。”
卯月之夜,草间雾霭使夜色更加朦胧不清。佐渡徒劳地掉转马头,反复小声自语:“可惜了……这种怠慢,也是一种不忠……迟了、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