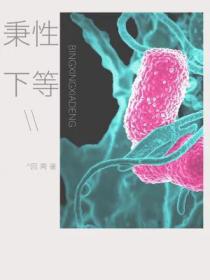南弦说,班长前两天联系他,说打算开个入学十周年同学会,知道他有我联系方式,让他来问我一声要不要参加。
高中那会儿我虽然不招人喜欢,和同学关系不睦,但到大学可能大家都是学乐器的,有共同语言,除了南弦外,同其他人相处还算融洽。
“在哪里办?”
“崇海天兴国际大酒店,你来我就把咱俩都报上去了。”
那日是周六,我休息,时间上倒是不冲突,就是地点有些远,在市区,从家里过去开车都要一个半小时。
“行,你报上去吧。”不过与其他从外地赶过来的老同学相比,这一个半小时实在不算什么。
到了定好的日子,避免市里堵车,冉青庄提前两个小时将我送到市区,车子停在酒店大门外的时候,离开席还有半个多小时。
一年前,区可岚在国外被捕,受到多项重罪指控,最后被判134年超长刑期,50年不得假释。
半年前,对我和冉青庄的严密保护便都渐渐撤除了。除了会有警察定时在住处附近巡视,其余生活与普通人无异。
冉青庄的修车行只在周一休息,其余时间都对外营业,今天也不例外。这几天活儿多,他每天都忙到很晚,我其实是不想麻烦他送我的,但他怕我自己开车危险,说什么也要送我。
“你回去吧,晚上我自己叫车回家。”
这么些年没见,班长还让大家带上自己的乐器,感觉是有很多节目要搞,会弄到很晚。他在楼下等我不合适,回去再来接我也不合适,还是我自己回去比较好。
“那你别喝太多酒,结束了给我发个消息。”从后车厢取出大提琴递给我,冉青庄大掌捧着我侧脸,俯身在我额头轻轻吻了下。
虽说车后方就是堵墙,我们夹在车和墙之间,不算引人注目,他动作又很快,不特意观察根本不会有人察觉我们在干什么,但我还是非常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下做这样亲昵的行为。
我的脸瞬间就烫了起来,如果现在我面前有面镜子,一定能照出我通红的面孔和脖颈。
“都两年了,脸皮怎么还是这么薄?”松开我的面颊后,他顺带揉了揉我的耳垂,“好了,进去吧。”
我点点头,背着琴往酒店里走。踏进旋转大门后,回头看了眼外头。隔着玻璃,冉青庄已经坐回车里,但车仍然停在大门外没有离去。
我朝他挥了挥手,看不清他是不是有回我,但不一会儿车就开走了。
班长包了一个大厅,足足安排了四桌。不仅是同学,连当年专业课教授都来了好几个。除了少数人在国外的赶不回来的,能来的都来了。
酒足饭饱,大家开始在席间走动起来,敬酒的敬酒,聊天的聊天,拉小乐队演奏的演奏,几个教授还给现场指导。
“季柠,你结婚啦?”
我回头一看,问话的是以前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特别活泼开朗的一姑娘,记得……是叫何誉。
她盯着我握着杯子的手,有些可惜地叹了口气道:“我还想着你要是单身的话,我一定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呢。”
我只当是开玩笑,毕竟她就是那种性格。
“南弦还单着呢,你要不要考虑考虑他?”我笑着与她碰杯。
何誉浅抿了口酒,冲南弦飞了个眼,顺着我话道:“行啊,等会儿扫个联系方式。”
南弦和她碰了碰杯,道:“扫个!”
虽是这样说,但她敬完了酒就头也不回地到别桌去了,并没有真的要加南弦的意思。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南弦放下酒杯,压低声音问我。
我们这桌本就没有坐满人,大多数又都跑到别桌去了,现在还在位置上的就留了小猫两三只,也都是各聊各的。
“什么?”
“何誉当年喜欢你啊。”
我本来想吃口菜压一下嘴里酒精带来的辛辣,听他这么一说,立马呛咳起来。
“你咳咳,你别乱说……”
南弦忙替我倒了杯温茶送到我手边:“真的啊,当年她还跟我打听过你的事。你每次去自习室自习,就没发现总能遇到她吗?有一次下雨,她还借伞给你。”
我一边轻咳一边将茶水饮尽,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她有次还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听音乐会,结果你说要打工没时间。”南弦一幅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我还以为你知道所以婉拒了她,没想到你个大木头压根没察觉。”
“她说那张票是多出来的……”
南弦发出一声冷笑:“那她一个女孩子还能说那票是特地为你准备的不成?”
我这个恋爱方面的菜鸟青铜被他反问的哑口无言。
到快十一点,班长提议每个乐器都组队演奏一曲,来为今晚的聚餐画上完美的句号。
大厅本就是个多功能会议厅,有舞台有投影。将谱子投到投影上,一支单乐器的合奏乐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产生了。
大提琴组一共就四个人,大家商量了下,决定演奏德沃夏克的《B小调协奏曲》。
我们的动静忒大,连下班的服务员都过来看热闹,门口挤了满满的人。
教授索性将门大开,欢迎所有人进来聆听。
最后一曲酣畅淋漓地演奏完,众人纷纷告别。
南弦开车过来的,直接下了停车场,在电梯里就与我分开走了。
深秋的夜晚已经有了萧瑟的寒意,空气吸到肺里,都觉得刮肺管子。
我下楼的时候,因为前头已经走了好几批,大门外不剩几个人了。何誉指尖夹着根烟,在角落的垃圾桶旁抽烟。
我刚想走到路边拦车,手机震动起来,冉青庄打来了电话。
“结束了?”他那边虽然很静,但隐隐可以听到一些喇叭声,不像在家里。
“嗯。你没在家吗?”
“等我一会儿,马上到了。”
我一怔:“你到了?到哪儿了,酒店吗?你来接我了?”
“对,反正也没事。晚上路好开,四十分钟就能到。”
我无奈地叹口气,道:“那你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身侧突然响起人声:“老婆打来的吧?”
我吓了一跳,握着手机转头,就见何誉站在我身旁,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正一脸打趣地看着我。
面颊一热,将手机收进口袋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面颊,道:“呃……是。”
何誉笑起来:“你别紧张啊,我又不是老虎,说两句话就能吃了你。还是你家教这么严,连和异性说句话家属都要吃醋?”
这倒不至于……不发火的时候,冉青庄还是很讲道理的。
“你在等车吗?”我努力搜刮话题。
何誉摇摇头:“我在等你。”
这回答一下子把我整懵了:“等我?”
“你可是我的意难平。”她面向我,眼里有些惆怅,“我时常想,要是当年我能鼓足勇气跟你告白就好了,要是我没有因为一场音乐会打退堂鼓就好了,要是我再积极主动一点……就好了。毕业后,我再也没遇到比你更让我心动的男孩了。”
我不知道这种时候该作何反应,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声“抱歉”。
她抿了抿唇,犹豫片刻,问道:“如果我当年跟你告白了,你会接受我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事。”
她问得认真,我思考得也很认真。
如果当年,在我遗忘对冉青庄感情的时候,她跑来跟我告白,我会不会同意?
有个人像冉青庄一样,关心我,驱走我的阴霾,听懂我的音乐,我会和对方在一起吗?
“不会。”我有些歉意地道,“但和你无关。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我所有的爱情,从那时起就都给了一个人,心里已经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何誉像是没想到这个答案:“你们是……”
“高中同学。”
眼角余光瞥到有辆熟悉的车驶了过来,停在了酒店大门外的私家车停车点。
“我的车来了,先走了,再见。”我忙朝何誉告别,背着大提琴快步走了过去。
冉青庄开了后车盖,下车帮我将大提琴放到后面。
“喝酒了吗?”他关上后车盖,问我。
“喝了一点。”
“我闻闻。”他突然靠过来,像只大狗似的在我脖颈处嗅起来。
“唉……”我别扭地向后避了避,不小心瞥到何誉站在原地,震惊地望着这边,眼睛都瞪大了,“好了,还有人看着呢……”
冉青庄抬起头,看了眼何誉的方向:“你同学?”
我点点头:“嗯。”
上了车,冉青庄几次往我这边看过来,欲言又止。我没忍住,直接先一步开口,问他到底怎么了。
他一边开车一边道:“她看起来有些伤心。”
因为她刚知道自己的大学意难平跟她一样喜欢的是男人。说伤心都是轻了,那简直是三观尽碎,再也拼不起来的凄凉。
“她大学,好像钟意我,但我完全没发现。”
冉青庄长长“哦”了声:“那确实值得伤心。”
“她问我要是当年她告白了,我会不会接受她。”我没有隐瞒的,将刚才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冉青庄。
正好遇上红灯,他拉起手刹,一脸严肃地看向我。
“你怎么回答的?”
我笑着凑近他:“我告诉她,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地占据了我的心,很早以前,那里面就再也装不下别的人了。”
他的眼里像是掺进了甜蜜的香草冰激凌,怔然片刻,便开始一点点的融化。
他吻住我,在大马路上,在信号灯前,在昏暗的车厢里。手掌按在后颈,唇舌炙热地交缠。
我微微眯起眼,任他亲吻,直到后头的车开始不满地按响喇叭,才推开他仓促地结束这个吻。
长吁一口气,他踩下油门,明显速度有比之前的加快一些。
“你累吗?”
“还行。”虽然已经快十二点了,但因为今天不是工作而是聚餐,心情是比较放松愉快的,也就感觉不到累。
“那就好。”
他意味不明地说完就不再开口,只是专心地开车。
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累不累,但到了家后,我就懂了——有体力,才好做别的啊。
如果这是游戏世界,回家前我的体力值是80,那随着时间推移,那本来还很充沛的80,在这个夜晚一点点走向贫瘠,到快天亮时,更是只剩下可怜的一点红血丝,只够我留口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