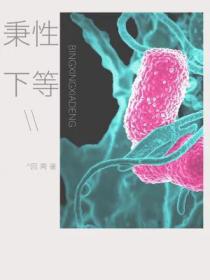林笙亲眼看着那颗跳动的心脏被放进了傅慈的胸腔,主刀医生不是他,但他做了最后的收尾,尽可能地没有给傅慈留太过狰狞的疤痕。
撤去林瑛琪的生命维持器前,吕馨希望儿子能再去看一眼对方,被林笙拒绝了。
这些年林笙已经不记得拒绝过多少次这样的提议,他不觉得去探望一具无知无觉的“尸体”会有多少意义,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真正有意义的,是他在做的事情才对。
当那颗更小,颜色也很鲜亮的健康的心脏被接上血管,重新跳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自觉在口罩的遮掩下,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夸张又兴奋地笑容。
对,这件事才是有意义的。
傅慈的身体和林瑛琪的心脏融合的特别好,在ICU呆了一周便转到了普通病房。
每次轮到林笙查房,他都会在傅慈那儿待得格外久。
傅慈醒着,他还有所收敛,只是做些常规的检查,搭个脉,听个心音。但如果傅慈睡着了,他会近乎贪婪地注视着傅慈的睡颜,肆意妄为地做他想做的事。
用最轻的力道掀开病号服,目光一寸寸描摹男人嶙峋的肋骨,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那块飘着消毒水味的纱布,妄图穿过它,透过皮肉,看到那颗属于林瑛琪的那颗心脏。
林笙俯下身,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去亲吻那道疤。虔诚的,如同忠诚的信徒对待他的神明。
等了十年,你终于在新的身体里重生了。瑛琪姐,我真的好想你啊……
他渴求着更贴近对方,鼻尖都要碰触到纱布。
“你在……做什么?”忽然,头顶上方传来沙哑的男声,语气带着些许被冒犯的不悦。
头皮一痛,林笙被抓着头发扯离了眼前的胸膛。眼里愉悦的光瞬间熄灭,再抬头时,他面上虽然维持着得体的微笑,心里却冷冷骂了一声傅慈杂种。
“你弄疼我了。”林笙软声道。
傅慈松开手,眼神锐利如刀,没有就此被含糊过去:“你在做什么?”他坐起身,又问了一遍。
“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刀口,看你睡得熟,没忍心打搅你。”林笙歉意地道,“吓到你了,真是抱歉。”
由于这十年一直用着自己那颗逐渐衰败的心脏,傅慈非常地瘦,不到人形骷髅的程度,但也与林笙记忆中那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有不少差距。
傅慈一粒粒系上自己的扣子,垂着眼皮,不认为对方刚才的行为简单一句“没忍心打搅”就能解释,但也没有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
“明天想喝什么汤?”林笙问。
傅慈没有亲人,同事朋友倒是不少,但人家也要工作生活,无法全天候陪在他身边,所以这段时间除了护工,反倒是林笙照顾他更多——不仅因为林瑛琪,林笙父母的嘱托也是主要原因。
“不用麻烦,我吃医院的饭食就好。”傅慈整理好了衣物,抬眼看向林笙。
“那怎么行?”林笙手指探向傅慈的面庞,在即将触碰到对方额前发丝之际,往下滑去,贴上了对方的颈侧,“就鸡汤吧,上次你难得喝完了,应该是很喜欢的。”林笙说着看向腕表,记录起心率。
他态度看着温和,其实根本不容他人拒绝。傅慈眼里闪过一丝厌烦,但没有再出口拒绝。
直到微凉的指尖被体温煨得微微发热,林笙才收回手指。走到床尾,做好记录,他说:“好了,你继续睡吧,我不打扰你了。”随后哼着歌心情舒畅地走了。
傅慈在医院里住了大半年,林笙每隔一两天便会送一次汤——都是他家保姆炖的。
在此期间,傅慈发生了一次急性排斥反应,所幸发现及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后遗症。但这么一折腾,花大半年养起来的肉又掉了不少,让林笙颇为不爽。
傅慈身体好了一些后,林笙也会推他去楼下的花园晒晒太阳,看看风景。傅慈总是拒绝,但只要林笙一说这对他身体有好处,他又会配合。
有时候林笙会觉得他真是个矛盾的生命体,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却很珍惜林瑛琪给他的“健康”。
他当然看得出傅慈对“活着”这件事很消极,但生命从来都是痛苦的。人类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死去,在痛苦中挣扎求生,亦或求死。
生命就是痛苦本身。林笙并不认为傅慈拥有免俗的权利,因此对方感到痛苦,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散步时傅慈向来沉默,林笙将轮椅往池塘边一停,他可以盯着池塘里的锦鲤看大半天不带出声。林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但看在林瑛琪的份儿上还是会耐心地陪在他身边。
“林医生……”
林笙和傅慈同时转过头,穿着护士服的年轻女人朝傅慈礼貌性地颔了颔首,示意林笙有话单独跟他说。
林笙当然认识对方,这是他的……情人之一。
“我很快回来。”他含笑对傅慈说着,朝女人走过去。
女人三十岁左右,身材很好,睫毛浓密,五官深邃,乍看像名混血,是谁看了都要夸一句“美丽”的长相,也是林笙十分中意的女性类型。
“找我什么事?不是说好了在医院就当不认识吗?”林笙和对方的关系始于一场团建活动,后来觉得彼此相性不错,就留了联系方式。
“我……我离婚了。”女人忐忑地抓着自己的胳膊,语气隐隐带着些期许。
林笙愣了一下,深深蹙起眉心:“然后?”
女人被他的反应刺痛了,咬了咬唇,道:“我知道我们之前的关系一直要偷偷摸摸,让人很疲惫。你愿意……愿意和我重新开始吗?你总是很关心我,对我很温柔,生日还给我买礼物……我知道我对你是不同的……”
林笙不是很有耐心地听她说完,嗤笑了声,算是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他将她颊边的一缕刘海归到耳后,表情怜悯,语调凉薄道:“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要娶你,就因为我对炮友还算大方?”
傅慈听到了树丛后响亮的巴掌声。他转头看去,过没多久,林笙黑着脸走出来,脸上顶着个鲜红的巴掌印——对方可真是用足了力气打的。
他揉着脸,表情十分阴沉,但一对上傅慈的双眼,便又春风和曦起来。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他双手搭在傅慈的轮椅把手上,道,“我送你回去吧。”
傅慈一言不发任他推着,行到半路上,忽然开口:“刚才那名护士之前我在急诊见过,手上戴着婚戒,已经结婚了。”
傅慈身为检察官,拥有优秀的洞察力与记忆力,林笙虽然意外他连这种鸡毛蒜皮的细节都记得,但也没有太过惊讶。
“是,她丈夫也是本院的医生,不过是口腔科的。”口*儿不错。
傅慈不再说话,像是不太在意。但林笙能感觉得出来,那天之后,仿佛确认了他是个不得了的核污染源,对方开始避着他,态度也更冷淡了。
正义的检察官大人,无法容忍别人做有违道德的事呢。
伪君子。假仁假义。
林笙面对傅慈时,态度依旧温和殷勤,但心里却无时无刻地不在唾弃、咒骂对方。
或许是老天对于林笙私生活混乱的一点惩罚。一个月后,同样的地点,女人的丈夫,那个年轻的口腔科大夫也找到了林笙。他离婚了,也离职了,来见林笙最后一面,抱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林笙懒得和他叽叽歪歪,直接将他同时和他们夫妻两个保持关系的事抖落了出来。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对方结结实实的一拳作为回报。
他舔着破裂的唇角,痛得姣好的五官都皱了起来。回到池塘边,等着他的是傅慈冷漠而又充满厌恶的目光。
好像在看什么不可降解的大型垃圾。
他压下就快冲口而出的,喷吐着毒液的蛇信,苦笑着在傅慈的轮椅前蹲下:“哎呀,不要这么看着我嘛。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了。”
除了医院里的躲不掉,他已经把他手机里的烂桃花全都删除拉黑,就不信其他人还能神通广大到找到他医院来。
傅慈盯着他唇角的伤,不咸不淡地开口:“你年纪也不小了,就没想过要定下来吗?”
“想过啊。”林笙甜腻地笑着,手掌暧昧地抚上傅慈的膝盖,“但也要问过对方愿不愿意……和我定下来。”
在那只手无法无天地就要探到大腿根的时候,被傅慈一把截获。他攥着林笙的手,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林笙的手骨爆发出剧烈的疼痛,像是下一秒就要折断。
他一下子就怂了,不住哀求:“好痛!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我跟你闹着玩的,真的……”
傅慈没有松手,他看着瘦削,手劲却出奇的大,林笙好歹也有一米八的个儿,竟然一时挣脱不了。
一个用力,傅慈拎着林笙的手,将他扯到面前。
“别打我的主意。”语带警告,他冷着声音,一字一顿道,“婊子。”
林笙的眼尾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两下,心里头已经把知道的脏话都骂了遍,明面上却没有立即发作。
他朝傅慈露出了一个非常“林瑛琪”式的笑容,嘴角含蓄地上扬,带动整张脸的肌肉,双眼微微眯起,将笑意浸透到眼底。
他们本就是亲戚,两分的相似在特意的模仿下,也能提升到四五分。
傅慈对着他这张笑脸,果真出神起来,不自觉便松了钳制。
“我和瑛琪姐挺像的,是不是?”他仰视着傅慈,反手握住他的大掌,覆上自己的脸颊,“没关系的,你可以把我当做她的替代品。”
他软言诱哄着,像只听话的小狗一样,蹭着傅慈的掌心。
傅慈垂眼睨着他,指尖微微用力,受到蛊惑般轻喃:“替代品?”
林笙眼里笑意更浓:“嗯……”还没来得及说更多,傅慈的手掌扼住他的下颌,将他未完的话尽数掐灭。
“……你也配?”傅慈目光鄙夷,似乎林笙光是言语上与林瑛琪相提并论就让他难以忍受。松开林笙的同时,他将他大力惯到一边。
林笙不受控制地跌在地上,垂着脸,刘海挡着眼睛,过了许久都只是维持同一个姿势。
“嗯,我不配,你别生气,生气对你身体不好……”闭了闭眼,指甲刺进掌心,他仍然垂着视线,眼里一片森冷,但说出口的话却又柔软又顺服。
说来奇怪,明明林笙在傅慈面前乖巧懂事,照顾他也算尽心尽力,但就像有着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林笙哪怕什么都不做,傅慈从见他的第一眼就认定了,对方是个画皮的妖孽。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并没有错,林笙的确不是善茬。从他们撕破脸又不算撕破脸的那天开始,林笙对他的骚扰便愈演愈烈。但不论他如何冷脸,林笙都不为所动,骂不听,赶不走。而他顾念林瑛琪,顾念林氏夫妇,纵然心中再不耐,也只得一再忍让。
林笙当然也看得出傅慈在忍他,可他并不在乎。他管傅慈是不是讨厌他,他又不是真的喜欢他。
哪怕傅慈拿最恶毒的言语刺他,羞辱他,他也不痛不痒——全当是野狗在吠了。
林笙以为自己清理干净了烂桃花,该不会再有人找上门。没成想旧情人是没找上门,旧情敌倒是先找到了他。
“当年的事,是我不好……”
季柠还是像以前一样讨厌,明明看到他表情那么恐怖,一副恨不得嚼碎了连骨头都吃下去的模样,还要假惺惺地为他牵线搭桥,让他同冉青庄再续前缘。
说话不这么咬牙切齿,他或许会更信服一些。
“好了,做了就做了。既然决定是自己做的,就别一幅好像别人逼你的样子。”感觉随时会被揍,这段时间挨够了打的林笙不想再跟季柠纠缠,倒退着拉开距离,主动结束了对话。
“让冉青庄别记挂我了,我现在……已经有别的喜欢的人了。”说完,冲季柠摆了摆手,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当晚林笙并不值班,但他还是留了下来,揽下了替傅慈记录心脏数据的活儿。
他让傅慈解开上衣,露出胸膛,观察他已经长好的刀疤。疤痕组织微微凸起,泛着与周遭皮肤不一样的红,但因为缝合得很漂亮,只是细细一道,并不狰狞。
他将冰冷的听诊器贴上去,傅慈颤了颤,没有躲。
其实检查并不需要脱衣服,听诊器隔着衣服也能听,但他想要更近地触碰林瑛琪的心脏,所以还是哄着傅慈让他把衣服脱了。
“今天那个人,和我没关系。”一边检查,林笙一边解释,“就是普通的高中同学而已。我和那些人都断干净了,以后只喜欢你,你千万别误会。”
傅慈的心跳平稳有力,没有一丝杂音。
任谁看到这一幕,都不会怀疑林笙是在和傅慈说话,但只有林笙知道,他在和自己的心上人对话,在和那颗属于林瑛琪的心脏对话。
林笙痴迷地凑上去,想要亲吻那道疤,被傅慈毫不留情地一巴掌按在了脸上,推离自己。
林笙笑起来,透过缝隙注视他,并不着恼,反而伸出舌尖,情色地舔舐起对方的指缝。
傅慈本就平直的唇角一下子往下更耷拉了几分,被毒蛇咬到了手指一样飞快收回了手。
“出去。”他冷声下逐客令。
林笙眨了眨眼,唇角勾出熟练的弧度,乖巧地起身:“好,你早点睡。”
如果说重遇季柠是“有点意外”的程度,那再次遇到冉青庄,简直就是“可以骂娘”的程度了。
傅慈康复出院后,被委派处理狮王岛的案子。上头怕他身体吃不消,想给他配个随行医生。
林笙主动请缨,医院里都知道他和傅慈是差一点成为亲戚的关系,因此并没有人来跟他抢这个职位。
他陪傅慈见过许多证人,也去见过那头被俘的老狮王——金斐盛。
金斐盛言辞凿凿,并不接受任何的辩诉交易。这就意味着,检方与他的律师团将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要打。
这让他很担心傅慈的身体,或者说,他的心脏。
为了方便护理,他们住在一起——当然是不同的房间。林笙每日清晨都会为傅慈测量血压和心跳,傅慈从不跟他废话,而林笙暂时也很满足于这种与“林瑛琪”身处同一屋檐下的状态。
然后,就到了那天。
前一天,林笙通过服务台收到了自己八年前送出的戒指。
他回忆了好半天才回忆起来这是送给谁的,不甚在意地转手就扔进了垃圾桶,隔天就遇见了冉青庄,身边还跟着季柠那傻子。
林笙瞥见季柠脖子上遮也遮不住的红痕,以为他们终成好事,不想进去讨嫌,更怕挨揍,于是非常识相地坐在了外头。
天气有些闷热,太阳很烈,林笙被热得心烦意乱,正好季柠出来给他送水,言语上一不小心,两人便争了起来。
其实也不算争,只是林笙单方面的输出罢了。
他就是看不惯季柠装模作样的,讨厌就讨厌,装什么客气?
讨厌一个人,就应该算计他,恶心他,将他珍视的东西毁去,把他打入深渊。如果做不到,讨厌的情绪只是苦恼了自己,别人却毫无所觉,这种事情比被不合意的人死缠烂打还要让他不能接受。
“现在你在干什么?自以为是地为我和冉青庄牵线搭桥?你真的是少恶心了。我只是被送出国,不是被送去坐牢,你知道我有多少机会联系他吗?”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注意到了门那边的冉青庄,但他没有停下,仍是无所顾忌地发泄自己的恶意,“别把你不要的东西塞给我,我又不是垃圾桶。”
冰水兜头罩脸泼下,透心凉。
“像你这种人……就该一辈子孤独终老。”这或许是季柠所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诅咒了,但对林笙来说却是不过如此。
“终于不装了啊季柠?你现在比刚刚有意思多了。”林笙笑起来。
季柠冷着脸转身往屋里走,拉开门就见冉青庄杵在那儿。
他慌乱地藏起杯子:“你,你怎么出来了?”
冉青庄没有回答他,将手里的车钥匙抛给林笙,道:“傅检让你去车里等。”说罢拉着季柠离去。
林笙嗤了一声,在大太阳底下晾了十来分钟的衣服,等差不多干了,他钻进车里一看镜子,脸都晒红了。
操,早知道不进去了。
他没好气地翻起镜子,将座椅放倒,一边吹着空调风一边闭目养神着等傅慈出来。
大概两个小时后,傅慈才从小白楼里姗姗走出,林笙早就一场午觉都睡好了。
“回去了?”他打着呵欠问。
傅慈轻轻“嗯”了声,拉下车子手刹,一如既往地公事公办。
回到住所时,停车位离电梯口还有一段距离,林笙就先下了车。
“林笙……”傅慈在他关车门前叫住了他。
林笙一顿,俯身看向车里:“怎么了?”
“我不关心你的过去,也不在乎你和谁有一腿,但别扯上我,也别影响我的案子。明白了吗?”
林笙有些委屈:“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这也怪我啊?”
傅慈脸上没什么表情:“你只要回答明白还是不明白。”
林笙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明白了。我也知道,你不会很轻易地相信我,但我对你是认真的。你和他们所有人都不同,你是特殊的。现在我只爱你,将来也只会爱你。”
“傅慈,我爱你。”
当他吐露甜言蜜语的时候,绝不会有人怀疑他的真心实意。
那眼神实在太真了,仿佛满心满眼都是你,为你生,为你死,只要一句话,便能为你付出所有。
但傅慈并没有就此沦陷,他自己的心已经坏了,现在的心是林瑛琪的,不属于他自己,更不会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只是眉心跳动了一下就让林笙把车门关上,没有发表任何感言地便扬长而去了。
“真是块难啃的骨头……”
林笙望着远去的车影,一点点隐去脸上的笑容,没有等傅慈,转身独自上了楼。
第二次再见冉青庄,是在医院里。林笙从傅慈的电话内容里得知一些大榕村发生的事,本以为是冉青庄受伤了,结果傅慈告诉他病的是季柠。
季柠竟然得了脑瘤。这世界,果然当个祸害才能活得久。
去见冉青庄的前两天,林笙和傅慈发生了点不愉快。
林笙的父母有时候会来崇海看他,家庭聚餐不免要叫上傅慈,对方也总会很给面子的前去赴约。林笙抓准了这一点,骗他父母有请,让保姆在家提前做好法式大餐,等对方进门,便拉他来了场烛光晚宴。
傅慈当即就想走,却被林笙接下来的话绊住了脚步。
“今天是瑛琪姐的生日,不该庆祝一下吗?”
傅慈皱眉:“今天不是瑛琪的生日。”他怎么可能连未婚妻的生日都不记得?
“瑛琪姐怕麻烦,一定是告诉你公历日期的,但我们老家大家都是过农历的。今天是瑛琪姐的农历生日,不信你自己算。”
他言辞恳切,有理有据,傅慈扫了眼桌上的菜肴,最终还是坐了下来。
虽说吃了饭,但傅慈全程没有一个好脸。
“大家现在好歹也算是同事了,用得着这么讨厌我吗,就连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林笙道。
傅慈低头安静地切着牛排,头也不抬道:“我和你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林笙默默翻了个白眼,道:“或许……我们可以说说瑛琪姐。”
随后不等傅慈发表意见,他自顾说起了小时候与林瑛琪的趣事。
有一次两人去动物园玩,他看到路边花坛里有朵很漂亮的小野花,粉粉的,和林瑛琪很配。他跑去摘,一转眼的功夫就和林瑛琪走散了。
林瑛琪找了他许久,都要急疯了,好不容易找到,发现他是去摘花了,红着眼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打完了,又接过他手里的花,说了声谢谢。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被打,没有哭,只是很震惊。
“……想不到现在天天挨打。”林笙说着摸了摸脸。
傅慈仍旧没有抬头,唇角却略微勾了勾。一旦涉及到林瑛琪,这位铁面检察官就会变得异常柔软。
林笙看着他,不自觉也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当医生,也是因为她。她说她小时候的梦想其实是当医生救死扶伤,可惜最后没考上。选专业的时候我就想,反正我也没什么目标,不如就替她完成梦想吧。这样,她一定也会感到高兴的。”
傅慈停下动作,从前林瑛琪也和他说过,如果当年学医就好了,说不定还能治好他。治好肯定不可能治好了,但她有这份心傅慈就很高兴了。
“当年知道她签了器官捐献书时,我其实有些意外,但想想,这确实是她会做的事。她一向很为别人考虑。不知道其他得到她器官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生活。”林笙盯着傅慈垂落的眼皮,意味深长道,“有没有对她……心怀感激。”
傅慈眼皮一颤,握着刀叉的力道更紧了几分:“会的。她是泥潭毒沼中普度众生的一叶舟,受她恩惠的人,都会永远记得她,感激她的。别人如此,我也是如此。”
说是这样说,他面上却并不见悦色。
对别人,林瑛琪是慈航普度的活菩萨,然而对傅慈而言,林瑛琪的心脏既是延续他生命的金齿轮,也是一辈子束缚着他的沉重枷锁。
林笙喝了口杯子里的葡萄酒,被傅慈窝囊的模样深深取悦了。
林瑛琪本想凭一己之力将傅慈带离苦海,想不到却促成了对方更深的痛苦。
他们就不应该相遇。如果林瑛琪没有爱上傅慈,就不会有这么多破事了。
“刀别停下啊,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林笙殷切催促。
一餐饭吃得还算和谐,傅慈走时,林笙送他到楼下。明天休息,今晚他睡自己家。
傅慈的态度因为席间谈论了许多林瑛琪有关的话题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不再满身是刺的防范,也能相对给林笙一个好脸色了。
或许他不过只是个不懂事的弟弟。这样想着,他同林笙告别,转身往停车位走去,才走一步便被身后的人拉住袖子。
他顺着力道回身:“什么……”
最后一个“事”字还在齿间,唇上一凉,林笙偷袭似的吻在他唇角。
好像怕被揍,他吻完就撤,速度快到傅慈甚至来不及发怒。
坐回车里,傅慈连抽好几张纸巾擦嘴,心里将刚刚建立的对林笙的评价全数推翻,
什么不懂事的弟弟,不过是个……
“小垃圾。”丢掉纸巾,发动车辆,他沉着脸骂道。
“你也就三十多岁,性格怎么跟我爸一样,这么严肃的?”
再见面时,两人气氛可谓跌到冰点。就算在去往季柠病房的路上,林笙都在试图化解他和傅慈的不愉快,但效果并不好。
“以后叫你‘叔叔’得了,反正你也做不了我姐夫了。还是你更喜欢我叫你姐夫?”他凑近傅慈,嬉笑着叫了他一声,“姐夫?”
傅慈忍无可忍地给了他一个眼刀:“滚开。”
林笙识相地退后,笑道:“我就是开个玩笑,别动气嘛傅叔叔。明天我爸妈让你去吃饭,你看有没有空……”
傅慈只以为他又在耍什么花样,厌烦道:“要是我让我发现你再假借你爸妈的名义让我去你家……”
“傅检。”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冉青庄出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之后,就有些鸡飞蛋打。
很难说林笙不是在主动讨打。要还债,总是免不了挨打,就和他所有的烂桃花一样。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故意说了些刺激人的话。
挨打之前的话虽然纯属挑衅,但被打之后的话却是字字肺腑。
当年冉青庄自己稀里糊涂,给了他空子钻,现在又装深情给谁看?把错全推在他身上,自己就真成了愚蠢的王子,可以向世人声称所有错误的选择都只是受到了邪恶魔鬼的蛊惑是吗?
“够了,我不是来围观你们演偶像剧的……”傅慈出声终止了这场闹剧,他警告林笙,不允许他再说一个字,“你父母的面子是有限的,别逼我跟你撕破脸。”
林笙仰着头,面颊和腹部火辣辣地疼,他注视着傅慈的双眼,知道他是认真的,只得乖乖闭起嘴巴。
同上次一样,他拿着车钥匙回车里等傅慈。一个小时后,傅慈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淡淡扫了他一眼,视线在他红肿起来的面颊上停留片刻,看向前方。
“你真该庆幸你的情人们都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杀人魔。”
林笙挑了挑眉,摩挲着下巴,迅速明白了他的言下之意——不然照他这么欠,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
他噘着嘴,故意示弱,委屈地盯住傅慈。
傅慈用余光也能看出他这是有话要说,便道:“你可以说话了。”
“冉青庄不是我的情人。”林笙顶着红肿的面颊,哀声道,“我们就是……读书的时候有点误会。”
傅慈闻言不予置评,驱动车辆平稳地驶出了停车场。
到了外头马路上,他才再次开口:“你不需要和我解释。”
林笙笑了:“但我还是想要和你解释。”
林笙不关心别人的死活,季柠明天死还是后天死,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他是医生,已经很习惯死亡,所以当傅慈告诉他季柠的病不是绝症时,他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不,要说感觉,还是有的,但不是对季柠,而是对冉青庄。
这家伙运气可真好啊。林笙想着。他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他爱的人再也没醒过来。
“傅慈……”林笙注视着眼前安静吃饭的男人,想问他嫉不嫉妒,羡不羡慕?是不是每天晚上夜深人静都在默默的流泪,被同死亡所分隔的思念折磨,叫不甘和懊悔充盈胸膛,每分每秒都在煎熬地活着?
傅慈抬起头,神色淡然地与林笙对视。
他现在养得很好,身上长了不少肉,虽说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面色还是不大好看,但和之前季柠在医院里看到的残废模样已经天差地别。
林笙看着他英俊的面庞,将那些恶毒地诘问又咽了回去。
“……我在你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支打火机,你是不是偷偷抽烟了?”
傅慈倏地蹙起眉:“你翻我的口袋?”
“只是看它在脏衣篓里,所以想帮你一起洗,别把我想得那么变态嘛。”林笙笑笑道。
傅慈并不信他的鬼话:“你知道我们是有家政的吧。”
林笙“投降”似的举起手:“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傅慈最后都没解释打火机的由来,林笙看出他不想说,知道自己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只好乖乖闭嘴。
金斐盛第一次庭审那天,休庭期间,傅慈偷偷从林笙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林笙在室内找不到他,开始到外头找,越找越是烦躁,最后发现对方正在和季柠交谈。
一见到他靠近,傅慈原本轻松的表情便一点点冷凝下来。
林笙心里冷笑了声,故意讨嫌般没有眼色地继续走向两人。
看不出季柠这小子还挺受欢迎,还是说……正义的勇者都喜欢这种类型的?
他一开始其实也装得挺像,要不是那些烂桃花……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心情突然变得烦躁,林笙注视着垃圾桶上的烟蒂,不再伪装自己,冷声道,“不是让你别抽烟的吗?”
“马上开庭了,我先回去了。”傅慈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只跟季柠打了招呼,说完绕开他就走了。
林笙暗暗握了握拳头:“你做任何有损健康的事,就是在杀死瑛琪姐。你已经害死过她一次了,还想再来一次吗?”
这话十分的重,傅慈回头的表情恐怖得要死,但他终于投注到林笙身上的视线,还是让林笙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满足感。
非得要刺痛到他才能正视我的存在,真是犯贱。林笙心里暗骂着,倒也不怕被揍。虱子多了不痒,挨揍挨多了,也有点习惯了。
但最终傅慈还是没有动手,这是法院,他不会因为一个小垃圾的三言两语就失去理智。压下怒火后,他一言不发地再次转身离去。
林笙知道现在跟上去完全就是讨打,闲着也没事,便有心与季柠扯了两句。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
季柠觉得他根本就是个神经病,不太想搭理他,但还是以一种担心的口吻,告知了对方傅慈的厌世情绪。
林笙还以为他一脸严肃要说什么,一听是这个,不在乎地“哦”了声,说了个更劲爆的消息。
“告诉你个秘密,他的未婚妻,是我的远房堂姐……也是我爱上的,第一个女人。”
季柠受惊的模样特别好笑,林笙欣赏着他无措而闪躲的目光,脸上笑意加深。
“所以他喜不喜欢我有什么重要呢?我喜欢他就好了啊。你们都把我当毒蛇猛兽,但我要的其实从来都很简单。”
傅慈不喜欢他没关系,反正对方这辈子也不可能再爱上别人。他要的不过是能同“林瑛琪”待在一起,更近更近,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摸到。因此和傅慈的纠缠,是不可或缺的。
他从来没想过要考虑傅慈的个人感受。从移植了林瑛琪心脏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傅慈这辈子,到死都别想摆脱他。
金斐盛的案子结束后,开了个不大不小的庆功宴,都是些检察院的人,也叫上了林笙。
傅慈没有喝酒,但林笙作为他的“代理人”被灌了不少酒。
喝得半醉的林笙光明正大地发着酒疯,挂在傅慈身上,吐露着自己对林瑛琪的爱意。
“我真的好喜欢你,我要的不多,你就让我待在你身边好不好……”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喜欢和爱,手掌贴在傅慈的胸口,五指用力,揪皱了原本平整的衬衫。
傅慈没有理他,扣住他的手腕,攥在掌中,只等电梯一到,将他扔进家门。
“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明明对你那么好……”林笙挣着手,哽咽着哭了起来。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掉,哭得伤心欲绝,涕泪横流。
虽说半醉,那也是醉,人一醉,就不太好控制情绪。纵然林笙一开始只是想装装可怜挤个两三滴鳄鱼泪,也经不住突然悲从中来,发自真心的哀恸。
“我知道我特别坏,我天生就是个坏种……可我已经在改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他用手背抹着眼泪,放声大哭,“我就是坏点子多,但我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傅慈个蠢货把你害死了,你能给他机会,为什么不能给我机会?我也爱你啊,我也爱你啊……
林笙脑子已经不清醒。
“别哭了。”
他收了一瞬,下一秒哭得更大声了。
嚎啕的哭声中,混杂进重重的一声“啧”。
电梯门一开,林笙便被大力扯了出去。傅慈开了锁,将他粗鲁地推进门内,随后扯开领带,绑住他的双手,半强迫地送回了他自己的房间。
林笙姿势变扭地倒在**,脸上泪痕犹在,抽噎着朝对方伸出手:“别走,别留我一个人……”
他睫毛上沾着眼泪,一双眼又黑又亮,实在是纯真又无辜。
傅慈看了他片刻,终究做不到对这张脸无动于衷,抽了纸巾将他脸上的鼻涕眼泪擦干净,又扯了被子替他盖上。
他做这一切时,林笙安静下来,看着他,眼里不再有算计,不再有怨恨,只是单纯地,静静地看着他。
傅慈替他解开领带:“睡吧。”
林笙眨着红肿的双眼,看着他笑了:“傅慈,我们就这样一辈子在一起吧。”
他拉过傅慈的手,将脸温顺地贴在对方手腕上,感受着脉搏有力的跳动。
傅慈一句话没有,只是用行动回答了他——他将手掌覆在林笙眼睛上,将他推开了。
随后他后退着站起身,沉默着与仰头看着他的林笙对视良久,转身离开了林笙的房间。
房门关上的瞬间,林笙酒醒了一些,他醉眼朦胧地冲房门露出一抹飘忽的笑,歪着头道:“呵,你逃不掉的……”说罢躺倒睡去。
几天后,傅慈以自己身体完全康复,不再需要别人照顾为由,向上头提出了免除林笙随行医生的申请,以此彻底切断两人的往来。
这手确实打得林笙措手不及,但他并不着急。这辈子这么长,他有的是时间浪费。
“带着愧疚与他纠缠一世”是傅慈此生都不要想摆脱的主题。
他们就这样彼此折磨,彼此需要,彼此躲避,彼此追逐着……度过这一生吧。